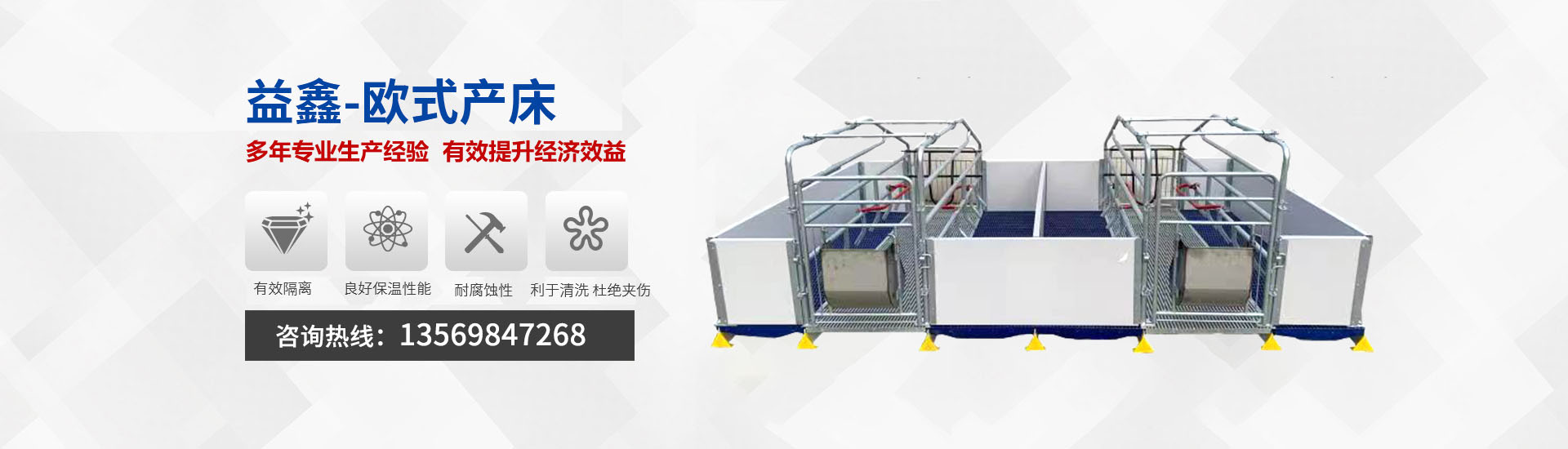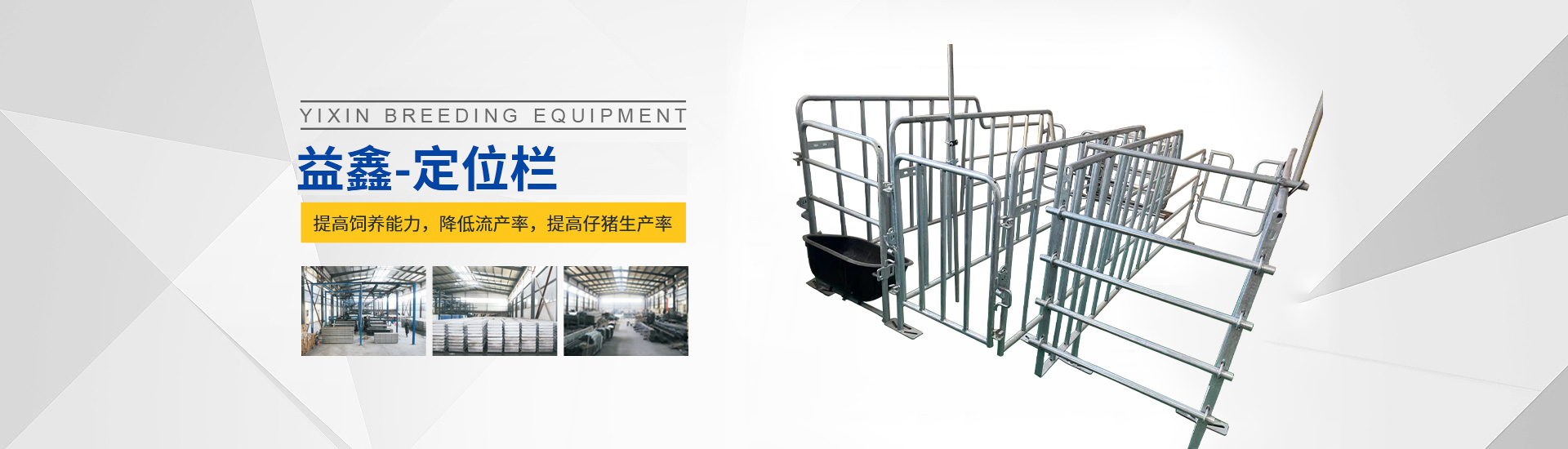躺在棺木里的分明是位开国将军,可身上穿的既不是那套缀满勋章的军礼衣,也不是什么高级西装,而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。
更让人看不明白的是,骨灰盒上空荡荡的,没盖那个标志武士最高荣誉的八一军旗,只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。
这不是礼宾司的作业失误,也不是家族不明白规则,纯粹是老爷子临走前留下的死指令:“不穿戎衣,不盖军旗。”
多少人一辈子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就为了身后能盖上那面旗,他倒好,走的时分非要跟那身衣服划清界限。
这事儿往深了扒,底子不是白叟的模糊气话,而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革新,对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前史“误读”最无声的反对。
跟他伙伴当师长的王光泽,那是和寻淮洲、乐少华这些赤军高级将领一个层级的人物。
乃至可以说,假如不算中心那段插曲,按他的资格和起步职级,这颗“少将”星的确挂得有点“轻”了。
其时乃至有风闻说,他在现场气得扯下了肩章,这尽管是别史,但也足以阐明他心里的憋屈。
段苏权的档案里,有一段整整三年的“空白期”,正是这段空白,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疙瘩,也是他从“赤军神童”跌落到“暂授少将”的底子原因。
故事还得从一九三四年说起,那哥时分的段苏权几乎便是开了挂的“天才少年”。
他和师长王光泽带着八百多号人,四百条破枪,要在贵州那一带声势浩大地搞作业,意图只要一个:让军认为赤军主力再这儿,把敌人引过来,好让主力部队安全搬运。
在四川秀山的那场惨烈包围中,段苏权的脚踝被子弹打得破坏,骨头渣子都露在外面。
部队被打散了,师长王光泽为了保住这棵独苗,把他托付给了当地老乡李木富,自己引开敌人,终究被俘献身。
整整九个月,要饭、睡猪圈、被人放狗咬,硬是一瘸一拐地挪回了湖南茶陵老家。
那时分老家也乱,他父亲为了保他的命,只能让他去乡公所干杂活,乃至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,想让他完全断了革新的想法,老老实实当个农人。
直到一九三七年,全面抗战迸发,段苏权传闻赤军改编成了八路军,心里的火又着了。

当他站在老上级任弼时面前时,任弼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——由于再安排的档案里,段苏权早就“献身”了,乃至连追悼会都开过了,姓名都刻在勇士名录上了。
这本该是个“英豪归来”的剧本,但在考究安排程序的部队里,这却成了他档案上的硬伤。
尽管任弼时作证让他归队,但这三年的“”阅历,在后来每次政治检查和军衔鉴定中,都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
哪怕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把冀热察军区带得风生水起,在东北战场上指挥纵队横扫千军,但在某些刻板的考量系统里,他始终是一个“有着杂乱前史问题”的人。
在东北战场辽沈战役期间,由于机场控制权的问题,他敢跟上级拍桌子争辩,乃至由于战术不合被通报批评。
这种“刺头”性情,加上档案里的瑕疵,让他在一九五五年的评衔中显得方枘圆凿。
看着那些从前跟在自己后边的下级都扛上了中将牌子,而自己这个当年的师政委却要为了少将军衔“谢主隆恩”,换谁谁心里能爽快?
他把精力都发泄在了作业上,不管是去搞空军建造,仍是后往来不断驻外使馆作业,他都干得极端超卓。
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,作为志愿军空军的高层指挥员,他乃至亲身上天去探索空战规则,那份陈述尽管指出了其时空军战绩计算的水分,开罪了不少人,但也正是这种敢讲真话的劲头,才让他显得分外宝贵。
他不需要那身代表等级和待遇的戎衣来验证自己,也不需要那面军旗来背书他的战功。
他挑选盖党旗,是由于他感觉自己从十四岁入团、十八岁当师政委,这辈子忠实的是那个崇奉,而不是那个评衔的委员会。